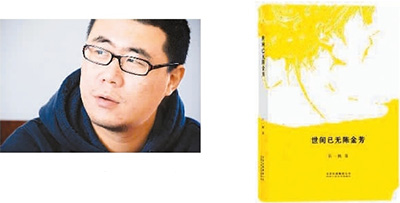
石一枫和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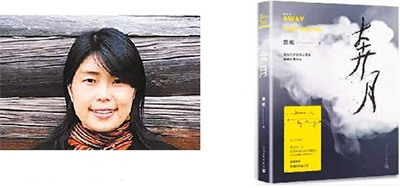
鲁敏和她的《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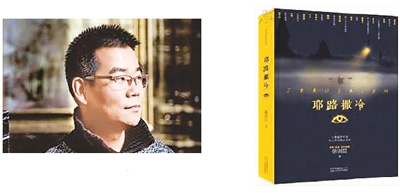
徐则臣和他的《耶路撒冷》
在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中国青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特别高。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青年,他们亲历了时代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尚的改变。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内心起伏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关于“80后,怎么办?”以及文学写作中“失败青年” 的讨论一直不绝如缕。这一代青年人如何从一种虚无与颓废的普遍情绪中脱身,如何完成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成为更加强大、完整的自我,成了异常显豁而重要的问题。
青年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曾经历了由“多余人”“忏悔贵族”到理想“新人”的转变。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青年人对于自我价值的确认与建构,必须经历一段异常痛苦的挣扎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迷茫、彷徨、不确定,然而只有经历并超越了这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新人才能真正塑造完成。
作为一个标志,石一枫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十月》2014年第3期)中的主人公陈金芳已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之一。小说中的陈金芳来自农村,进京后一方面受尽了同学、家人的凌辱,另一方面,凭着惊人的毅力、胆量和一意孤行的果敢一步步改头换面,最终变成了举止优雅、颇具姿色的女老板。目睹她窘迫的家室和困顿的少年时代的“我”,在20年后再次偶遇陈金芳。此时的她已经改头换面,成了艺术品商人陈予倩。此后,“我”多次出入陈予倩的饭局、宴会,见证了她八面玲珑的社交名媛生活,也最终目睹了她因为诈骗败露而自杀未遂及至被捕的过程。陈金芳到陈予倩的发家史复杂、隐秘而不为人知,在看似奇迹般的成功背后,埋藏的是由欲望、虚荣和孤注一掷、不计后果所构成的深海炸弹。小说中的陈金芳经历了短暂的盛放和悲剧般的凋零,然而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奋进,一种改变命运的努力,一种生命的原始力量感。她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她明知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想要改变命运何其艰难,但是她始终不畏血泪。
几乎在同一时期,我们见到了初平阳。如果说陈金芳的身上散发着一种草根青年在面对命运时毫不犹豫的行动力,那么,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主人公初平阳则代表了这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犹疑和迷茫以及一种在内心世界中不断自省与忏悔的精神。小说中的初平阳以及他的朋友秦福小、景天赐等来自相同的故乡,成年后的他们如同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乡村来到了城市。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童年的伙伴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他们面对着各自的现实困境和精神挣扎,最后,秦福小留在了花街,其他人再度离开,那个具有无限意义的大和堂,在众人的一致同意下交给了秦福小。借此,这些心怀愧疚的童年玩伴们完成了有限度的自我救赎。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历了“到世界去”又“回到故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更是一种漫长而艰辛的自我确认。如果说“到世界去”是如今现代化与国际化形势下大多数青年人的共同理想,那么,经由“回到故乡”,青年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根,也清楚了自己为何离开,又最终应该回到哪里去。在故乡,他们回溯自己的童年与过往,痛苦地却也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恶,进而忏悔,并最终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虽然小说的结尾依然充满了困惑和困难,但正是经历了这种寻找和确认,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才能获得新的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
在文学的世界中,“出走——回归”不仅是一种经典的叙事结构,在内在精神层面,重返的宿命更似一个魔咒,最终将人们带回了此刻与当下。在鲁敏的小说《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中,主人公小六在车祸后主动制造了“失踪”,这也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重新认识她的机会,不管是丈夫贺西南还是曾经不为人知的情人张灯,在寻找小六的过程中,都完成了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重新认识。小说最后写到,“她总算是实现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逸走了。她一无所知,她万有可能,就像聚香刚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对于小六来说,与其说这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重生。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确认。小六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出走,而是回归。如果小六就此隐遁乌鹊,那么她不过是无数逃避现实的逍遥派人物之一。比这种逍遥更重要的是,她在深知现实的平庸与坚固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家。如同生比死更艰难一样,回归比出走更需要勇气。我们相信,再次回归之后的小六真正认清了自己,她的内心积攒了能量,完成了涅槃,因而成为内在精神世界的强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短暂的逃遁与永恒的回归,虽然对于改造现实并无实际意义,但在内在精神层面却完成了关于“拯救与逍遥”的辩证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书写青年一代内心的苦闷、挣扎,书写他们在生活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人生态度,成了一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写作主流——如同青年人正在面临的现实的挣扎一样,这是一个痛苦的生长、酝酿与积蓄的过程。直到近一两年来,一种具有内在力量感的时代新人形象逐渐浮出水面。孙慧芬的小说《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中,主人公张展在父母、亲人、“交换妈妈”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但在同学申一申、聋哑学校的老师、癌症病人等另一些人眼中,张展几乎就是天使。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青年身上巨大的撕裂感?孙慧芬以一个作家的无限耐心结结实实地接近了她笔下的人物。因为父母都是政府官员,张展从小就享受着无忧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父母对于权力的过分信仰、追逐,一方面让他们疏于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自以为是的教育方式,强迫张展面对他们所铺就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一个以不断的自我沉沦报复家长的孩子,忽然遭遇了命运的重击。父亲飞机失事,让曾经沉沦、叛逆的张展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同学于永博和他癌症晚期的爸爸,又将张展推向了真切可感的生活现场。在那些被需要的濒死之人、残缺的孩子们身上,张展看到了希望,也得到了力量。
正如《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中所说,“《寻找张展》是近些年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小说将以最为罕见的饱满可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张展这一形象,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下青年的另一个面向。以张展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在面对现实时勇敢地迎上,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抗现实的残酷、生命的无常。正是这种勇气,让他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拯救的能力,也让他终于看到了个体生活的希望与价值。消极颓废地活着其实一点都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挣脱、超越沉重的现实和肉身,如何找到生活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感谢张展,正是他痛苦的蜕变和主动的自我救赎,让我们终于在当下文学中看到青年人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
托多罗夫在评价巴尔扎克和他笔下的人物时曾说,“与其说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说是他‘创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会,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与他们碰面”。不管是陈金芳、初平阳、小六或是张展,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一次次让我们想起自己身边的青年人。我们不断地书写他们,不断地在生活中与他们碰面。他们或许正在经历物质世界或个体生命的艰难,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向往。他们是痛苦的、挣扎的,但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思考现实、反顾自身的。正是在这些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属于当下时代的“新人”,看到了一种力量正在缓慢而稳固地积蓄着。(行超)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
 提起小剧场话剧,傅维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绝对信号》到《恋爱的犀牛》,从人艺小剧场到国话先锋剧场,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北京青戏节,从李六乙到孟京辉、田沁鑫……小剧场诞生三十多年来,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一个标志性人物都与这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
提起小剧场话剧,傅维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绝对信号》到《恋爱的犀牛》,从人艺小剧场到国话先锋剧场,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北京青戏节,从李六乙到孟京辉、田沁鑫……小剧场诞生三十多年来,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一个标志性人物都与这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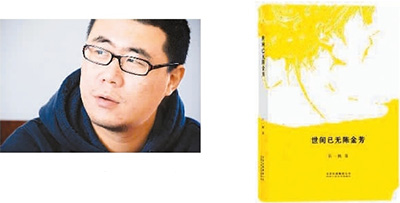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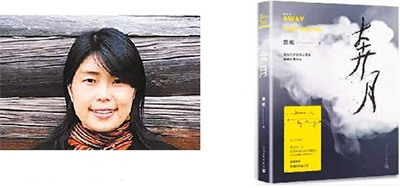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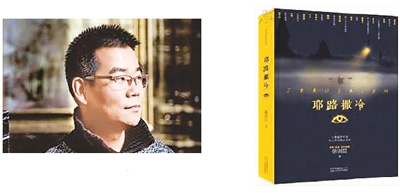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