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鹏程述学》龚鹏程著
《龚鹏程述学》是一本由传统走向未来之书。
传统,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龚先生把六艺作为书的目录,来说明他在这些领域都学到了什么,又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前者是师友渊源,大综合、大继承;后者是批判取舍,开创,自成一格。
俗话说“大匠不示人以璞”,可是龚先生毫不忌讳,现身说法,藉着怀念老师的方式,隔体传功,金针度人。
而更能度人的,是指出向上一路,要求在心胸志气上提升。说他老师“最讨厌我为赋新词强说愁,亦不喜欢我作苦语或耍小聪明,经常痛责我:余最厌此等。青年吐属,如何可以有此?青年少年强充情种,中年以后叹老蹉卑,皆是俗物”。又以诸葛亮为教,说:“诸作结语均大衰飒,甚非所望于仁仲者也,亟改亟改!从诸葛公淡泊宁静中想象其光明俊伟气象,勉之!”这就不只是教作诗,更是教做人了。
把做学问跟做人结合起来,正是龚先生学问的特点。所以他看不上文献的、客观的、只会做逻辑演算而行事糊里糊涂、自限于学科划分的学者。
龚先生述学,可以不避忌谈他自己的失误,诚恳自剖,实话实说,光明洒落,实在非常难得。除了在学理和知识方面自我反省之外,他对自己做学问的心态也有许多省察,说:“那时,我正提刀踌躇,接战四方!如今我当然很后悔这盛气好战的毛病。”又说:“我写过的文章比谁都多。性质猥杂,各式各样。有深言,有浅语,有正餐,有杂拌儿。大抵皆有益于人、有用于时,但也不免有些只有游戏或应酬的价值,甚且常为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最精彩的,是他引龚定庵“伤生之事二,一曰好胜、一曰好色。好胜之事三,曰学问、曰憎怨、曰荣利”那一段。说:“批评我的人都责我好胜。是的,谁不好胜呢?凡自以为不是庸人的,都好色好胜。做学问即是好胜之表现,或以好胜之心为底子。学者之炫耀知识,与才士炫文采、富豪炫奢侈、女子炫妖丽,有何不同?而学问做得好了,荣利便来。或别人给你奖项奖金名衔,或生起荣利之心,自己去争取。黄金屋啦、千钟粟啦、颜如玉啦,盼个不了。做不好,则被人憎、被人骂、被人耻笑,自己又憎怨耻笑我憎嫌我的人,往复相煎,遂若寇仇。学界本是读书人的组合,似应最纯皓、最具理想性,而其实到处都争来斗去,争地盘、抢位子,黑函蜚语横行。就因其中憎怨与荣利搅成一团,所以是最大的名利场与是非圈。日居其间,其不伤生者稀。因此,谈到做学问,我首先就要劝人莫做。若真有点有天资,可以做学问,则再要问能否戒色、戒憎怨、戒荣利,转学问伤生为‘学以养心’。做不到或不愿做,则干啥都好,千万不要治学。我炫学争胜,毛病最甚。幸而还有点自知之明,所以能由此反省起,渐渐转出学以养心这一境。”
这一段,真是可圈可点,可当全书“句眼”读。不但是所有读书人的药石,也是龚先生自己的方法。
龚先生博通三教、兼贯九流,但大家既佩服他博大,又认可他是醇儒,即是因为“反身省察”这种功夫,乃是古代儒家特有也最强调的。现今读书人的本领,只在书上,不能通过反身而求来提高自己,所以不是为己之学。龚先生过人之处,便在这一点上,处处可以见到这一方法的运用。
龚先生的名气,大多来自他的博学,三教四部六艺九流,当代鲜有人能像他这样兼通。所以大家最常夸他的,就是这个。但《述学》中这一类叙述,却让我们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的知识储备好、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写论文从来不用獭祭鱼、查资料,可是他更看重的不是知识,是心;不是技术,是道。
龚先生经常流露的孤独感,或许就由此而来。
他用生命来呈现他由传统得来的生命,在传统消失的时代,当然孤独,不被理解。可是他因拥有传统,所以孤独而不寒苦,反而热力四射。掉臂独行,自己发光,做着倔强的孤独者。
但这看来还只是序曲。致敬传统、传续传统,乃是要由这根子上开花、结果。近代沧海橫流,谷物都淹死了,他却要再栽出灵芝來。
故他谈六艺、谈经学,跟一般讲国学的人不一样,强调的是要由其中长出东西来:“质疑经学不能开展出现代学术的人可多啦,我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做个反证。”所以他每一卷都在讲如何开展的问题。如诗,早期是学诗、作传统诗;后来就做现代传播,并结合西方文论,发展属于现代的诗学,继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与西方对话。
因此他讲国学,独树一帜,绝不是复古冬烘们能比的。他对西学传统、现代社会、后现代思潮之熟稔、深入,在两岸国学领域中,也是极少见的。
这其中,既复古又创新,两者融为一体。他做得兴高采烈,我们则还雾里观花,看不明白,得要一点时间消化消化。幸好,《龚鹏程述学》就是他治疗现代病、重开礼乐文明的纲领,我们可以仔细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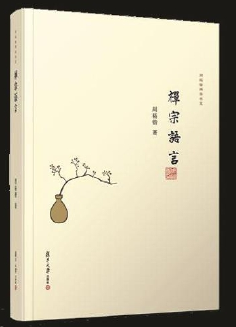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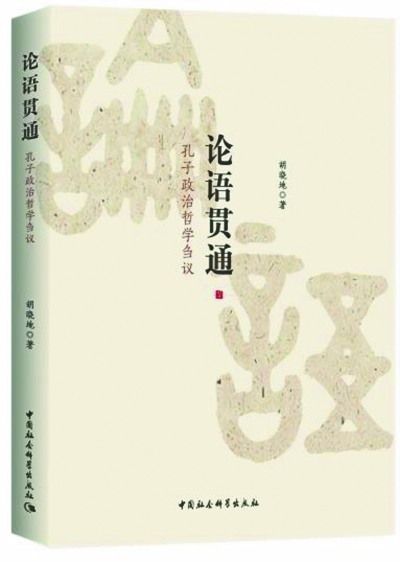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