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国藩先生对做学问要求很严。“我想开始写论文,但是余先生对我说:利玛窦他们都是懂拉丁文、希腊文的,你也应该懂。所以我又去学了拉丁文、希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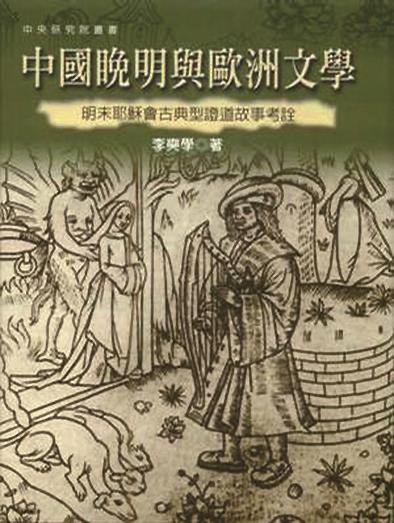
台湾“中研院”的李奭学研究员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明清中西文学交流,提出了“没有晚明,何来晚清”之问,认为现代“文学”一词在中国的内涵是晚明天主教与晚清基督教合力建构的结果,晚明的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近日,《文汇学人》特约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狄霞晨老师对李奭学研究员进行了访谈。
李奭学认为,中国旧有的文学概念,跟现代人所谓的“文学”没有关系。晚明学者杨廷筠用“文学”来表示“文科”,此时的“文学”已经不是“文章博学”的意思了,有了窄化的倾向。“文学”这两个字,如果没有杨廷筠有意无意地改用,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地现代化。
李渔笔下的书生已经举着望远镜偷看大家闺秀
文汇报:您在《没有晚明,何来晚清?》一文中,追溯了“文学”一词的现代性之旅。晚明传教士与现代意义上“文学”一词的形成有何关系?晚明和晚清的文学及思想有什么样的精神联系?
李奭学:“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这个题目我写了好几年。文学的现代定义是在误打误撞的状态下从西方进入中国的。晚明西方传教士艾儒略、高一志他们谈的“文学”分为四个范畴: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自撰文章议论。当时他们用的词是“文艺之学”或者“文科”。晚明中国学者杨廷筠为天主教辩护的时候,本来应该用“文科”两个字,但他有意无意地把“文科”改为“文学”,意思和前面讲的“文艺之学”、“文科”相同。
杨廷筠所讲的“文学”在今天看来似乎属于“humanities”(人文),但在当时已经是窄化了的文学概念。这个概念来自1599年欧洲耶稣会学校。史书在今天看来虽然不算是文学,但在西方的传统里却曾经是文学的一部分。在西方文艺复兴结束前,杜撰的内容是可以进入历史书籍里面的。比如,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雅典与斯巴达战争,写到雅典将军出征前的训话时,他就很明白地跟读者说:“下面这段话是我杜撰的,我认为他当时应该会这样讲。”这是非常后设的现象,作者居然跳进了历史叙述之中。再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写某国与某国发生争执,太阳神认为没有意义,于是去阻止。这也明显是虚构的。历史在西方一直是文学的一环,西方历史有很多是杜撰的。中国的史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史记》中写刘邦的母亲遇到蛟龙,产下刘邦,这也是一种虚构。《史记》中像这样的虚构很多,但西方历史中虚构的更多。所以文艺复兴前西方历史一直是文学的一部分。中国人过去也把历史撰述当作最高的文类。到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认为历史要有凭证,主张“科学治史”。古人的历史都是英雄的历史,但自从“科学治史”之后,历史学科就从文学变成了社会学科,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从文学院移到社会学院中去了。现在人口史、人口变迁都是历史系在研究了。历史在当时属于文学,“自撰文章议论”就是议论文、“古贤名训”也是文学。
杨廷筠是个小人物,一生做过的最大的官就是 “京兆尹”。他写的文章不一定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但魏源的影响力却不一般,他的《海国图志》(1852)在清朝九个行省印刻,红遍大江南北。继杨廷筠之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用“文学”一词指“文学创作”,他用的“文学”内涵与杨廷筠几乎是一致的。魏源说罗马本无“文学”,等到征服了希腊之后,“爰修文学,常取高才,置诸高位,文章诗赋,著作撰述,不乏出类拔萃之人”。就是说罗马把希腊的东西大量地转化为自己的,文学也包括在内。魏源在这里所理解的“文学”概念与杨廷筠非常相似。魏源应该读过杨廷筠的《代疑续篇》,但他不承认。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其实魏源看了不少明朝的西学。
1866年,“文学”被当作“literature”的同义词被德国传教士罗存德收录进了他在香港编的《英华字典》。这本字典很流行,台湾“中研院”的图书馆就有多部。罗存德的“文学”定义就是从杨廷筠、魏源他们那里过来的。很偶然,在日本传教的洋教士平文在和日本人一起翻译新的西洋名词,也用“文学”来翻译“literature”。平文在日本、澳门都待过,应该看过罗存德的字典。这样一来,“文学”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就出现在日本了。
在“文学”现代意义的传播中,力量最大的还不是传教士,是晚清的维新派、留学生、革命党,他们都聚集在日本。他们回到中国时,已经把诗、散文、小说当做文学了,在1903年左右出现了好几篇文章。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文章里,都出现了“文学”的新义。
中国旧有的文学概念,跟现代人所谓的“文学”没有关系。杨廷筠用的“文学”已经不是“文章博学”的意思了,有了窄化的倾向。“文学”这两个字,如果没有杨廷筠有意无意地弄对或弄错,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地现代化。
“文学”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晚清传教士吸收了很多晚明的译词。晚明与晚清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晚明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早期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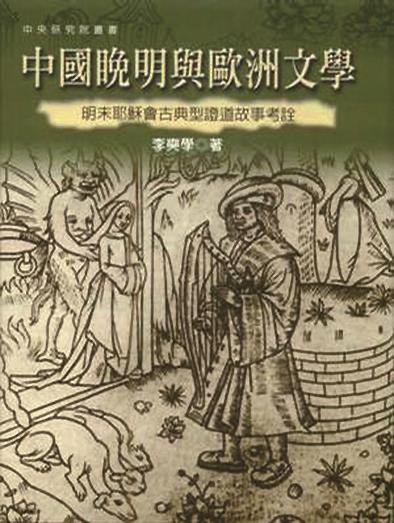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