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晚上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个好人了。”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监区时,狱内公示栏上印着监区服刑人员犯罪致死人数,他入狱时,曾让这个数字上升了一位。
陈家安的父亲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经过,只知道9年前一个冬天,原本在家务农的他跟同村一个绰号叫建娃的朋友走了,说要出去赚钱。陈家安小学肄业,修过路、挖过矿,但干的时间都不长。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说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点“麻烦”,就一起去“帮忙”。出发的时候3人各自在兜里装了一把小刀,当时他身边的年轻人中许多都有这个习惯,也是一种“时尚”。
陈家安已经记不清打过谁、被谁打过,只记得那是一条幽深的巷子,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两旁是居民楼,隐约有做饭的香味。出事之后,陈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几天后在茶馆被捕时才知道有人在那场打斗中失去了生命,指认现场时,地上有一大滩血迹,那时才感觉到害怕。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行凶的是“彬娃”,而陈家安也参与了打斗,被判13年。他被带走时,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
那次“帮忙”持续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他的人生却从此被改变了。
王国涛也曾让狱内公示栏上的数字上升一位。起因同样十分琐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觉得邻桌的声音太大,两桌人就借着酒劲打了起来,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离往往比被捕时来得更早。出事时王国涛的父亲还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几个月。邱迪在一次冲突中砸了对方的老虎机,并拿走了里面的钱,被判抢劫罪。他曾经在外潜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几年没跟家人见面,手机号换了好几个,出门会戴上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同样犯抢劫罪的杨严生活在单亲家庭,在大街上见到父亲他会装作没看见。陈家安离开家不久就换了手机号,因为“不想让父亲找到他”。
但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家成了唯一的主题。监狱民警会不定期对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进行“视频点名”,他们必须和家人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记他们罪恶的地方,没有人主动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亲结束,陈家安的父亲也没有向儿子问起当晚的经过。杨严每次说起自己的愧疚,母亲总会把话题岔开。张新然的哥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王国涛入狱的时候儿子还小,这些年他总是告诉儿子自己在监狱上班。
身体的记忆会不合时宜地提醒他们自己还是个服刑人员。尽管前一天熬了夜,陈家安早上还是不到6点就醒了。他习惯性地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在监狱整理内务一样,直到母亲夺下他手里的扫帚。在家短短几天,她只想让儿子好好休息。陈家安几年前患上了口腔溃疡,严重的时候疼得吃不下饭,体重比8年前轻了很多。
这几天,陈家安在大多数时候是个普通人,甚至带有更多的善意。服务员端菜上桌他会说“谢谢”,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请别人先走。只是总有一些场合需要他的真实身份。县城的医生问:“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检查?”他说:“在里面待了几年。”
“里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种获得普遍默认的暗号,对应的动词是“进去”和“出来”。
“出来了吗?”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希望能进行长期治疗。
“还要进去。”
第三天:十年巨变
陈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这一天,整个中国都在纪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亲历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陈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爷爷奶奶在地震中丧生,旧居如今已经只剩下一段残垣。
那时他刚刚出去打工。家在汶川县雁门乡的高山上,只有悬崖边的几亩梯田,早年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从国外引进的车厘子树刚刚栽下,需要好几年才能长成,家里生计困难,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还没“进去”。可是灾难的降临不分内外,大地在同一时间开始摇晃,四川省内多所监狱跟不远处的居民楼一起裂缝、垮塌,服刑人员们和普通人一样,冲出房屋的时候来不及带上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物品。被关押在阿坝监狱的杨朝华当时因杀妻刚刚入监一个星期,地震的时候正在监舍学习行为规范。他右手有残疾,原本对活着并不抱什么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应还是:跑。
一栋楼里几百名服刑人员从各个楼层往下跑,跑过平时需要听从指令才能越过的监舍、过道、大楼的一道道铁门,一直跑到空地上。远处依山而建的围墙正在垮塌,但没有人继续往前跑,那块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很多人说,那一刻他们唯一想争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运的是,四川省内靠近震中的几所监狱都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几小时后,所有服刑人员已经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铺和被褥也被搬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棚子底下。那块空地就是他们的监舍,点名依然每隔一小时进行,睡觉、起床都有口哨作为提醒。对服刑人员来说,阳光和空气既是自由,也是束缚。灾难为他们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笼。
在当时,“牢笼”不只是存在于监狱里。由于地震,灾区的许多道路无法通车,通讯也已经中断,许多还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赶回监狱,在路上穿过漆黑的隧道,睡过拥挤却安静的集装箱。回家的路陈家安整整走了两天两夜。
对监狱来说,这座天然的牢笼并不可靠。几天之后,受灾最严重的阿坝监狱开始了对服刑人员的“千里大转移”,把服刑人员分批次转移到其他监狱。杨朝华是最后几批被转移的服刑人员之一,他记得天不亮就被带上一辆大巴车,跟邻座的服刑人员戴同一副手铐。两侧车窗都被报纸遮挡,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何处。从茂县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经无法通行,只能绕路,平时几个小时的车程走了整整一天。为了确保押解途中的绝对安全,服刑人员被规定中途不能下车,车上有一个移动马桶,为了不上厕所,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喝水进食。直到将近凌晨,车子才驶进崇州监狱的大门。
陈家安的跋涉也终于到了终点。到家时,爷爷奶奶已经遇难,他和家人在废墟中挖出了遗体。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风俗,他们在去世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对木棺。被发现时,遗体和木棺一起被压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特地开展了一次震后离监探亲活动。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丧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终生残疾。汶川博物馆里常年播放着地震一瞬间地动山摇的视频资料,陈家安的妹妹看了几秒就捂着嘴跑开,他在后面默默递上纸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几乎找不到一点往日的影子。经历过地震和入狱的双重灾难,他对家乡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从那年开始,四川监狱的离监探亲工作开始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并且走在了全国绝大多数监狱的前头。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观”,鼓励监狱通过各种手段激励服刑人员改造,各地再次大规模试点离监探亲活动。10年来,每年崇州监狱都会在春节安排服刑人员离监探亲。而从今年开始,频率和人数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间接促使四川监狱加快了“从山区到城市、从田间井下到车间教室”的转移速度。震后,崇州监狱已经从距离城区几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转移到了城区西郊,监区与居民区仅一墙之隔,几百米外就是喧闹的菜市。以前监舍的通铺也改成了上下床,监区内有了电视、书架和心理咨询室,以及规范化的小学课堂。
陈家安和杨朝华就是在监狱内获得小学毕业证。杨朝华今年刚刚符合离监探亲的全部条件,原本也申请了离监探亲,可是因为剩余刑期还有4年多,风险较高而未能获准。
“盼了这么久,还是没盼到。”他所在的车间正在加工月饼礼盒,这让他更加失落,因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饼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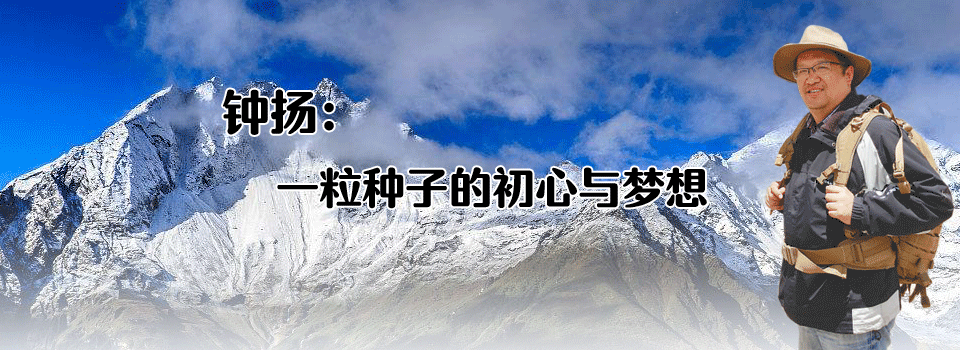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