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离监探亲工作开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错纠错机制还不够成熟,监狱民警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很大。”崇州监狱民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也是很多监狱多年来没有开展这个工作的原因,怕‘惹麻烦’。”四川监狱系统却一直在坚持,12年来批准了4387名罪犯离监探亲,全部安全按期返监。
地震之后,陈家安曾经“非常听话”,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后,真正的牢笼还是来了。
第四天:与家和解
今年的母亲节是5月13日,陈家安在入狱前从来没为母亲庆祝过这个节日。这天他决定,自己去地里采摘车厘子,让父母在家休息。车厘子树早已长得老高,并成为了汶川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家里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年车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时候,陈家安觉得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帮家里做的事情了。
家庭带给他的并非像这短短几天一样,只有温暖。父亲从小对他很严厉,印象中从未表扬过他,也从未有过像样的沟通。邱迪的父亲因为他逃学,曾经把他捆起来送回学校。
杨严的父亲曾经在打他时把衣架都拍断了,下岗之后经常喝酒,有时会“发酒疯”。他和姐姐从来都是匆匆把饭吃完,避免跟酒后的父亲说话,“他都说一些很无聊的话题,比如让我们以后去当工人”。他入狱之后,父亲曾经写信给他,责备他不听话,还把自己曾经得过的“先进工人”荣誉证书复印给他看。杨严当场撕得粉碎,跟母亲说不要让父亲继续写信了,“那么多年都没管过我,现在倒要管了”。
这次回家,严厉的父亲们都老了。杨严的父亲还住在离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里,他和姐姐的房间一直没动过,曾经玩过的沙袋和双截棍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监狱里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都带在身上,摆了满满一桌子。父亲仔细端详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说“好”。他下岗之后做了厨师,做好一桌饭菜总喜欢问孩子们“好不好吃”,也曾想听到一声“好”,但孩子们总是显得很不耐烦。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话题跟以前一样少,父亲最终说带他们出去散步,绕着新修的公园走了两个小时。
邱迪已经听不懂轮椅上中风的父亲说的话,只能靠猜。张新然的母亲在得肺癌之后还坚持去监狱看过他,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他记得母亲以前是个很讲究的女性,喜欢浅色的旗袍,现在却终日卧床,头发全白了。而王国涛永远见不到父亲了。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在没人的监舍跪着哭了一个多小时,面前摆了几根香烟,权当祭奠。他曾经梦到过父亲带着笑容说“终于回来了”,却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对服刑人员来说,“父亲”这个身份很难有机会做得更好。王国涛的儿子不爱说话,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总是“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干脆不应”。他把原本夹在驾驶证里的儿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里,时常想起从前开车的时候,儿子喜欢钻在他握着方向盘的臂弯里。作为父亲,如今他只能从一张张照片中感受儿子的成长。这次回去,他特地带儿子去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泡温泉、看电影,儿子只喜欢看喜剧片,生活给的悲伤已经够多了。
张新然的女儿不愿意让父亲拉自己的手。开家长会时,女儿每次都跟老师说“爸爸出差了”,她已经“快编不下去了”。
邱迪曾经有做父亲的机会。当时他尚未入狱,女朋友已经怀孕5个月了,最后还是做了引产。“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没有父亲”。
杨严很讨厌别人说自己像父亲。尽管他们都有些急躁、固执,还都当过兵。他唯一一次记得来自父亲的关怀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亲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一路都不停点头,希望对话赶紧终止。相比关心,他更能记得父亲的过错。
这么多年,他始终没叫过父亲。探亲结束之前,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勉强叫了一声,心想“叫就叫吧”。他说自己出狱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去看望父亲,但“很可能没时间”。
第五天:“自在”与自由
陈家安离监探亲已经到了最后一天。监狱规定在下午4点半之前必须返监,否则以“脱逃”论处。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别并不忧伤,甚至有些轻快。他申请了假释,如果获准,他就随时能跟家人重聚。
回监那一刻,陈家安觉得释然。关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经跟社会脱节,走在外面总觉得惶惶不安。大多数人入狱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朋友圈,也没有打车软件。王国涛打车送儿子上学,下车前还在掏钱包,妻子悄悄跟他说“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监狱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开始,却也让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自由,不用奋力追赶时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员已经习惯了监狱规律的生活。监狱里每个人都是一串编号,任何行动也都有缜密的轨迹。陈家安能流畅地背诵整本《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手册》,即便回到家里,有人问起他的编号,他依然会不自觉地把右手抚上左胸,那是他的番号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监狱之后,他说:“出去不自在,回来才自在。”
监狱的生活也让他们重新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世界。探亲期间,邱迪特地去书店买了本《货币战争》,他在监狱曾经看过这个系列的其他分册,很感兴趣。入狱后,他突然发现以前自己过得浑浑噩噩,“金融危机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年他自学了素描,经常临摹其他服刑人员的家人照片,画完就送给对方,却从没画过自己的家人,“觉得拿不出手”。陈家安喜欢打篮球,高瘦的他是前锋。杨严每天劳动结束后都要在监区前的篮球场跑步1小时,读书笔记做了十几本,衣兜里总是装着一支笔,他说“想活的面积更宽广一点”。
通常用不了太久,参与过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就能彻底跟家人团聚,最长的剩余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太多“自在”的时间了。服刑人员之间有独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见面先问一句:“你还有多久?”现在的杨严会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有3个月。”他觉得自己刑期将满对别人是一种伤害。他发现,通常关系好的服刑人员刑期都差不多,这样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
陈家安有时会想象自己出去以后的日子。母亲已经亲手绣了几双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柜里,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给他未来的孩子准备的,尽管他还是单身。在他老家,结婚生子依然是一种成熟的标志。陈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没有结婚,准备等他出狱再办。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他,还给他带过照片,他欣喜地夹在几十张家人的照片里,时常翻看。只是对方没等到他出狱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为“名声已经不好了”。杨严的母亲跟他聊起这些,他说,“现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时候”,“还是事业为先”。
陈家安原来想过出狱后放羊,因为“赚钱快”。现在只想先踏踏实实帮家里种车厘子。杨严喜欢旅游,出去后想先痛痛快快玩几天,“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做了两年老病残监区的监护员,现在的邱迪觉得“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长短,在乎质量。”他显得坦然。
几年前,杨严的姐姐帮他把QQ账号昵称改成了“倒计时”,签名就是他剩余的刑期,每年改一次。进入最后1年后,签名变成了每个月改一次。现在停留在“3个月”。他自己在心里把这个单位变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减去一位数字。数字越变越小,他却不敢再想了。因为“越想时间过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陈家安迷迷糊糊醒了过来,睁眼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家里。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着那片黑夜,他突然觉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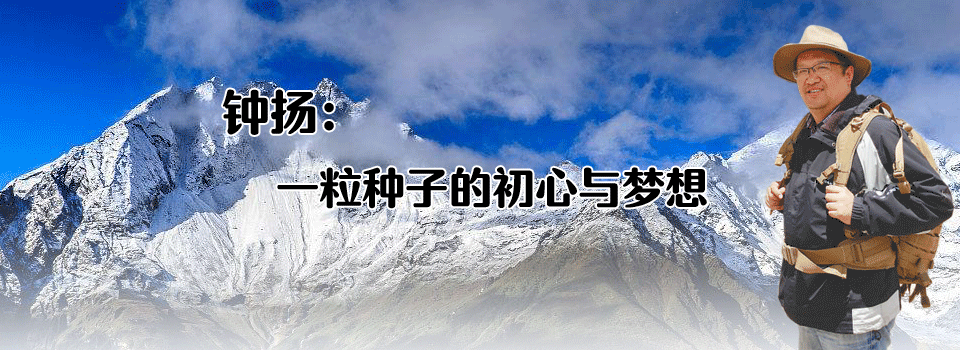










 ×
×